|
刚才你讲的是对的,鲁迅确实是超越了一个“具象”的层面,把握了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阿Q》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作品。绝对不是一个看着很愚昧的农民,像那个《阿甘正传》那样的,这完全是两回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哲学论文。但是这个抽象和哲学又不一样,这个里面的文学性又非常具象、栩栩如生,非常的具体。具体性是由阿Q的一点小事,点点滴滴的小事、傻事、笨事——一会儿被人打,一会儿想要打人嘴巴子、一会儿在那儿做白日梦、最后被人砍头时才想起来叫“救命”—不要小看这个结尾,阿Q的“救命”是和狂人的“救救孩子”一样重要的大事,都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都是打破历史循环的新的道德起点。只有出现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我们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同样,只有阿Q死掉,那个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救命”才能被人听到,二十年后的那条好汉才会有新的生路。这些都在“寓言”的层面上运行,就是所谓Allegory,讲的都是抽象的概念,形态又不抽象。就像狐狸吃葡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是个寓言概念,这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有狐狸、有葡萄,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但是这则《伊索寓言》并不提供给我们关于狐狸和葡萄的动物学、植物学的知识,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让我们直接的、一下子获得一种抽象的概念,但是又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 所以讲阿Q是一连串的寓言故事,每件事都是小寓言,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一类像《伊索寓言》一样的故事。那么寓言一般来说,这是从本雅明到德勒兹都说的,“小文学”、“政治性的文学”、“集体性的文学”、“颠覆性的文学”要讲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鲁迅的写作肯定是要讲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东西,从《呐喊》自序里面就看出来整个的一生和近代中国的关系——心中的郁闷、寂寞、愤怒、希望和绝望,讲出来的话他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地说我只是做一个“一流 ”就行了,这不是鲁迅的抱负,这肯定是讲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大到一定程度了,这个东西是会把常规意义上的文学给“压垮”的。常规意义上的散文、小说,这种文体没有办法负担那样的道德重量,或者生存意义上的重量、政治意义上的重量,愤怒都承担不了——鲁迅一愤怒起来就不会设计短篇小说的情节,太罗嗦、太雕虫小技了。直接就是什么《为了忘却的纪念》、《淡淡的血痕》不都出来了么?但是因为他要讲的东西那么大,所以他就一定要找到那个最具体的形象,所以他肯定是allegorical、是寓言式的。 还有一个很现成的寓言写作是《圣经》,宗教最经典的文本往往都是寓言故事。它对应的是symbol这个词,象征。“象征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所以意义都是圆满的。然后每一件事都和另一件事有关系,我们可以把世界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而且可以呈现出观念和现实之间的统一体。寓言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统一体的。当中国这个文化的世界、价值的世界、物质的世界、生活的世界还在一个统一体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写章回小说,可以写曲、写词、作诗,你怎么“玩”怎么好。就看唐诗宋词,那点东西很简单,我每次读唐诗宋词我就想,我第一次坦白,我做学生时候自己看这些古代文学经典心里暗吃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真了不起,你读完以后还是觉得了不起,我觉得现在我又开始读古典文学,非常感动。我读那个东西读得非常感动,但是你会发现那些都是“小小的东西”。你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么伟大的传统,最多的作品是离别、思乡,就是写那种很“小”的东西。写边塞之苦,也很具体、很“小”。那后面支撑的世界,像“盛唐气象”得整个文化脉络在里面,就象征着整体在里面。所以怎么写都可以,怎么写都在“文化的建制内”,它可以充分的个性化,可以充分的特殊化。鲁迅却不是。鲁迅这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所以它只能以这种“意象拼接”的方式,抓住一个意象是一个意象,然后让那个意象承担它根本没有办法承担的状态。这样的写作就是“小东西”,他大也大不起来,大了就太麻烦了。所以鲁迅经常说“我搭不起这个时间”,实际上说的是“我做那事干嘛”,要在一个太平世界,要是没碰到过“青年朋友的血”、“骨肉”、“连呼吸都呼吸不出来了”,也许考虑做长篇小说、写点像样的东西。那离真正的文艺有多远鲁迅自己心里很清楚,鲁迅经常那么说。但是他这个不是道歉,而是“我有更重要的事”。“更重要的东西”,那只能是寓言故事,以小见大——寓言最简单的特点就是以小见大。借此可以以小见大、指桑骂槐、你就可以抓住一丁点的意象,残垣断壁、一点点小的边边角角的东西,但总之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东西。《阿Q》很有逻辑性,确实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生产的逻辑,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大作品。可是大作品因为它是小文学,正是因为它小它才大。鲁迅真的写一篇关于江南小镇上农民的愚昧、落后的长篇小说,写上、中、下,写上个几卷,那可不行。可能很好,那样我觉得就没有阿Q了。 郜元宝:那我问您一个问题。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关系的问题上,我第二次听你这个表述。我想起04年读到温儒敏的一篇文章,他是说建议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者要充分尊重当时发生过作用的一些批评家的声音。他是以他的“得胜的文学史家”的优越性(来提议)我们也要关注他们。(张:照顾照顾他们的利益。)让我想起今天你谈的贯穿着的思路,就是你实际上是要“悬置”很多东西,其中文学史是一个很大的部分。你所谓的充分的解放文本,实际上还是解放批评的力量。那我不知道你说的本雅明所针对的当时德国的批评和文学史的两个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在中国的情况似乎是,批评家是很亏的。他们身先士卒,很多批评家在我的眼里已经老去了。很多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进入文学的运动,提供一部分最鲜活的感受,但是最后都烟消云散了,最后得胜的还是那些在高校中的文学史家。就这样把他们收编了,结果一排比就变成“大家”了。我的这个抱怨实际不单单是我的,是很多作为“炮灰”的批评家们他们普遍的抱怨。这个在中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不知道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就是难道是因为一个体制允许文学史压抑批评?或者说在我们中国真正有大的批评家起来了,可是我们知道俄国文学有许多大的批评家,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文学史家。那么在我们中国的情况,(张:也就中国知道,中国的大文学家外边也都不一定知道)我想知道是不是一个体制性的东西。光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也很难选择。这是一个问题,等会儿希望您回应。 第二个问题我也有一种怀疑,就是“作者已死”。作者能不能“悬置”?据我所知,很多中国的鲁迅的读者,他们之所以对鲁迅的作品感兴趣,是完全借助于他们对于鲁迅这个人的想象(张:这个我知道),他们“不允许他死”。那么这个“不允许他死”这个值得面对的问题(张:就是鲁迅害怕的问题啊,你像《野草》里“死后”多可怕,死了以后别人还不让他死,是不是?)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你讲的所谓的神学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的神学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可以通过“神的所造的世界”来认识世界,像保罗神学的一个制度化,从创世纪的神的永恒,“他所造之物皆显灵”,他又害怕人们沉湎于他的“所造”而忘记创造者,所以他说“你们既然知道崇拜被造之物,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崇拜造物的主”。他的这个两个表述更主要的还是说你要直接的崇拜造物主。我们把这个神学问题借用到文学批评中来,那么现在所讲的那个“作者已死”,它能不能够一劳永逸的把作者“悬置”起来?我很不凑巧,我读了很多鲁迅的书,但是我一旦碰到某个考证者说“考证了鲁迅的某一个细节”,我会毫不犹豫的放弃鲁迅的书去看这个“细节”去。这是我想起我内心有一种冲动,我对于无论是真实的鲁迅的存在还是虚构的鲁迅,我总是有一种难以忘怀的眷恋。这个眷恋恐怕是文本无法夺去的。这点东西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说。 张: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很好的问题。其实本雅明谈到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另一点也很重要,他说:文学批评是原点,文学史是派生的。他有个前提。你看德国浪漫派中我们今天作为文学史来读的大家,像施莱格尔兄弟、诺瓦蒂斯、包括谢林,甚至黑格尔,他们首先是批评家,他们是在运动当中的人。也就是后来在被当作文学史来读的那一批德国浪漫派批评家,他们就是德国浪漫派本身的灵魂人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创造出这个文学运动里面的人。可是他们的判断最后以“史”的形式可以存在,但是也可以以其它的形式存在——以美学形式、以批评的形式。那这个先不去说它,本雅明把文学批评抬得很高,抬文学批评贬文学史,这后边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于文学批评有一个界定,就是文学批评绝对不能成为文学写作的奴仆。真正伟大的文学批评都不是跟着文学作品走的,它是有自己的逻辑。我们读真正好的文学批评,绝对不是说他在怎么复述作品、描述作品、评价作品,而是说它以一个完全来自文学之外的一个逻辑怎么样跟作品逻辑发生关系。我们看批评家都是看批评家的东西,而不是看批评家怎么说作品。就这一点你刚才说作为“炮灰”的文学批评家,当然很值得同情,但是有一点还是他们把自己看得太轻。他们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说出了 们没有想到的东西,让他们看到后觉得“哦,原来我写的是这个”,他没有达到这一层的话,他们也不是成功的批评家,这是一点。那么老温讲的那个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看到这个变化基本上还是一个学术体制的问题,因为你看30年代不是这样的。你说30年代时候写《新文学大系》的那些导言,当时那些人都在,像郁达夫编散文的话…… (郜元宝:很有意思,很多人从他们编的《新文学大系》导言中得到的是后来成了文学史一样的东西,而实际上那是些文学批评的东西) 张:其实完全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实际上可以作为文学史知识来领悟的,这是“好的意义”上的文学史,那么当然已经发生的事我们今天肯定从一个历史的脉络上去读,但是这个主次要搞清楚。如果最后所有的东西只是浓缩为一个二三流的学者用干巴巴的语言写的那么一段“某某某在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那还有什么意思?我也看得很气愤、也很郁闷。就好像所有的东西最后的裁判是以这种经院哲学的那种毫无血色的、毫无生气的,没有任何判断、任何趣味的东西。刻薄地讲,中国一多半搞文学史工作的也许本来都不该入文学行当,我想你要他们去做中国会计史,他们也一样做。如果他们对文学没有特殊的感觉和“判断力”,只是在一个学科层面,在碰巧被安置在上面的这个“岗位”上做“史”,今天这个工程、明天那个项目、翻来覆去地编教材,那文学史就同会计史、广告史,公共交通史也没有什么区别,区别是偶然的,但对文学学有兴趣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偶然性的。 (郜元宝:但我插一句,很多批评家也就是因为有着批评家的体制在里边。) 张:是这个问题,好像一有作品我就应该写点介绍、简介。开会拿红包的批评家、跟作者吃吃喝喝的那种批评家或者怎么样,他们也不把自己当一回事,所以这一点也不太值得同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你看博兰兑斯写的欧洲文学史,你说是批评还是文学史,我看就很难说。当然这属于批评,但是这也是文学史的一个非常好的(范本)。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真正好的文学史,真正有效的文学史,让人读着觉得有用的文学史,都是时间上非常短的、在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史。不可能你写30年、60年、100年,那就是纯粹学术体制里面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像博兰兑斯讲19世纪,真的讲得不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讲朦胧诗的那几年,好多文学史我会非常喜欢看、非常有用。从批评、从审美、从判断,更不要说从其他传记意义上的、历史意义上的知识、材料,你会得到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样的那种一定不能做“工程”来做的文学史,那种就没有意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上帝”那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关键,那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这就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文学里的作者和宗教里的上帝毕竟还不是一回事。这里面的区别很关键,因为任何的宗教最后的“底牌”是你要“敬畏”你的上帝、你要怕它。就像马基雅维利说“你光要别人尊重我还不够,你要别人来怕我”才行——“尊敬”你可以第二天不尊敬了,但是“怕我”你永远怕。上帝是比一个暴君更暴君的一个暴君,他要求所有人都怕他。你看所有的《圣经》故事里面那么多残忍的事情,就是要你“无条件的敬畏上帝”。这个在文学里面是不存在的,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我们干什么要敬畏作者?我们干什么要怕作者?这是一层。你讲的第二层我是非常理解。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要从理论上要承认“作者已死”——并不是说我心目中没有鲁迅的形象,或者我对他没有敬意的判断、没有感觉到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或者想像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最简单的说,我对鲁迅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对这个形象是有自己的信念的。这是我们凡是读鲁迅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点,没有这个东西我也不相信能做出什么好的鲁迅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文学研究者一定要像个婴儿一样,我们和鲁迅的关系要有个所谓“精神断奶”的问题。很让我觉得有点不理解的现象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断奶”。鲁迅是一个很“滋养”的源泉,离了鲁迅就完全没有安全感、没有方向感,没有道德上的确定性,然后成天这个“先生、先生”叫得我很提心吊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断不了奶”的时候你怎么研究鲁迅,怎么读鲁迅?那么跟作者平等的关系、文学性的阅读、打开文本,那个什么都谈不上——你还没有“断奶”呢!(“精神断奶”很重要),真正的研究鲁迅的人身上一定要有点“鲁迅气”,要有点“叛逆气”,要有点“直面虚无”——“没有路的地方”我就站在那儿。如果鲁迅是条“路”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研究鲁迅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做鲁迅研究是鲁迅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是道德合法性的源泉,这都是已经把重读鲁迅的前提给毁掉了。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孙向晨(哲学系教授):我对这个文学批评是一点都不了解的,但是你刚才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印象蛮深的:就是包括竹内好读鲁迅,是“文人读文人”。实际上在中国很多文学批评里面还值得一看的,还是那些很多文人气的、文人读文人的东西。那你刚才介绍的应该说是伽马刀、核磁共振,一串都是相当学科性的,其实是把文学批评当作科学了。当然这个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的意思,但是是一个很强的学术训练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学科批评”。这个确实是,我觉得会造成很多问题。文学批评就是“某回事情”,它不仅仅是作为文人说要体会作品,它其实是要有一些“利器”的,而且这个“利器”打穿之后是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出来。那么就是说,以你这些利器去“搅和”鲁迅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所有理论都是从西方这里过来的,你读鲁迅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嗑牙”的地方?就是“嚼”上去好像有“嚼不碎”、让你“嗑牙”的地方呢?其实意思就是,理论不可以把它消化掉的,它是剩余的一些东西。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张:很好的问题。这点肯定是有的,没有的话我倒要怀疑自己,真的。这肯定就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我前面说到的“知识的悬置”什么的没有人能做到。其实我自己读鲁迅也有很多“嗑牙”的地方,有很多知识准备不足的地方。就比如说鲁迅和佛教的关系,我对佛教是一点也不懂;还有他和章太炎的关系,等等——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我先从边边上面讲起——在这些准备上,他有一些话我不是很明白的。在这一点我承认。就像他跟着章太炎做学生那一段,怎么读古文、对佛教怎么看,包括他在《朝花夕拾》里面提到的他对于民间戏剧、民间的生活方式、他童年的一些回忆……比如说这句话我就不是很懂:像他在《阿长与山海经》里面他最后说到“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是非常感人的一句话,但是你怎么讲也讲不出意思来。比如,我那个生硬的讲法就从本雅明那里的“意愿记忆”、“非意愿记忆”而来,我说鲁迅还有第三层记忆。除了那个普鲁斯特式的那个让触觉、嗅觉一下子把人从理性的链条上解放出来,然后回到回忆的空间。我觉得鲁迅在“遗忘之下”还有一层记忆,那个我觉得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种对“母体的眷恋”,这个是跟鲁迅表面上的知识形象都是不符合的。这个最难讲。那次在北师大讲,被学生追问得最厉害——到底是什么东西?传统?还是“恋母情结”?文化回忆还是文化遗忘?这是鲁迅回忆的“第三层空间”。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更虚无的虚无”呢?还是对于一个家园的最未来的指向呢?——最回不去的一个家往往是“放在最前面的”,“回家的路最远”,是不是这个东西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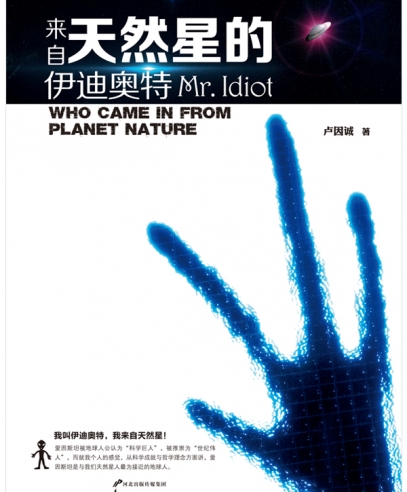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