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点是“打开文本”,UnpackingtheText。这个意思八十年代后期先锋小说 苏童、余华、格非他们都讲过,苏童说写小说就像叠纸鸽子一样,文学或艺术就是这么个东西,细心的读者会把它展开,看迭缝,这是读苏童他们小说的一个乐趣。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打开鲁迅的文本,跟所有既有的、更确定的阅读方式都发生关系,但是都不一样。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内,包括民间学术,其中一些非常有活力的阅读方式和鲁迅既定的阅读方式都不合,但都有借鉴的作用。比如“经典阐释”这个路子,鲁迅文本当然是经典,但读鲁迅不是读柏拉图、不是马基雅维利,也不是读孟子,鲁迅文本是个文学作品,作为“写作”来读和作为“经”来读这是不一样的。其次,把鲁迅作品当作纯粹的学术史材料来读。我们大量的研究、所谓“鲁研”这个体制,大部分东西是学术史材料,这个工作有意义,但基本是个准备性的,不是说对一些老先生不尊重,但它确实是个学术史“材料”。同时,我们绝对不要把鲁迅当作“文学赏析”来读,拿鲁迅做“赏析”是跟他不太沾边的。最后,打开文本不是去欣赏或崇拜一个道德形象。我们很多人读鲁迅其实触摸不到文本,直接进入到了“先生”这个道德形象的沐浴当中,跟一个虔诚的教徒和上帝间的关系一样,这样就没有文本的问题了。鲁迅是思想资源,但单纯把他当成一个思想资源则不可取,因为这个思想资源在认识论意义上终究是有限的,它是有时代性的,而不是没有时代性的。相反,吸取这个思想资源的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文学性、形式、文本、写作这样的范畴,因为在语言实践的层面上,从审美判断的层面上,鲁迅写作中包含的自由和可能性,要比鲁迅思想里的道德提示丰富的多。单纯从鲁迅的文本中抽出一个口号来、抽出一个立场来、抽出一种态度来、抽出一种人生观来,这是对鲁迅的一个极大的压缩和简化,而不是完整的把握。 文学文本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就是细读、慢读。一定要细,一定要慢,做形式分析、句语分析,把审美自律的问题和历史、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就是多元决定论的问题,多重决定,就是同时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但多元决定也有“过度”的意思,本来一个就可以决定的,可是它有三、四个因素,最后形成的结果就不是个“合力”这么简单,这里面有种重复性、重迭性、交叉性。 文字风格的辨析,这个还是很一般的,很常见的方法,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如果我们要把它作为文学去处理的话,在读者和作者的关系之间——就像“知识悬置”一样,这是个比较主观的进入的路向——一定要坚持“作者已死”,作为作者的鲁迅是个死者,他不是作为一个活着的上帝、先知到现在还在指点我们,改怎么走、怎么读、怎么想,什么是有道德的、什么是没道德的、什么是保守的、什么是激进的。鲁迅只作为一个死了的作者,我们惟一能和这死去的上帝发生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个上帝留下来的世界,借用神学的观点,我们能理解上帝的惟一途径是领悟、把握上帝的世界,整个世界是上帝的物化,道成肉身。我隐隐约约感觉到鲁迅对这一层是有考虑的,《野草》里有《墓碣文》这一篇。墓是洞开的,自己看着自己的墓志铭,尸体自己躺在里边,身体都打开了,这是个什么形象?鲁迅文本实际上整体上也要作为一个“墓碣文”来看的,他死后所有的东西都要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文字、文本来看的,更不用说鲁迅《野草》的整个意象,他不愿意做个“老不死”,要通过自己的消亡来获得生命。承认作者已死是阅读鲁迅的一个基本态度。这是个前提,也只有这样才能进入文本。作者不死,我们进入文本就是见作者去了,作者死了,剩下的是我们和文本之间的事,没有作者的事。 这里面还有两层意思。第一,阅读鲁迅是我们和鲁迅文本的关系,不关任何人的事,尤其不关鲁迅的事。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和作者是绝对的平等关系,不要仰视。当然也不要俯视,现在有人要把鲁迅从神坛上拉下来,这毫无必要。平视就可以,或者干脆把他放在括号里面,把他悬置起来。第二层意思就是,进入文本是我们和文本之间的事,这个“含义”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在文本中最后做的是:通过文本把自己打散,然后在文本的另一头、在阅读的终端把自己再重新聚合起来,看看第二次收获的自己和在进入阅读之前的自己有什么不同,这是阅读的增值的过程。这是保罗•利科的一个最经典的阐释学(论题),读者怎么进入文本的问题。这在隐喻意义上也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人进入世界后无时无刻不在“守住自我”,那个被守住的自我是个完全没有生产性、完全没有意义的自我,那就是我等于我,只有我,每天和别的东西混合起来、揉合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失去了自我,变得异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世界的散文的一部分的那个我才有意义。我们跟鲁迅的文本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通过“我”的阐释学的不断的重新确立,鲁迅的文本是活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而不是我们活在鲁迅的文本中间。 第二点更简单,就是文本的解放。这两者有因果关系,一旦作者死了,文本中所有的多义性和歧义性、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无限性和有限性在我们的意识里都是须要分析和探讨的。鲁迅作为一个解放了的文本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也好,对当代中国的思想生活也好,都是有意义的。而以往的鲁迅阅读,正是由于强调作者或者文本自身的实体性,都多多少少、有形无形、有意无意的把它限制在了一个位置上。 我想今天对鲁迅的重读应该可以在这些方向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我先讲到这儿,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讨论继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问答部分 郜元宝(主持人):现在是3点20分,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不管大家感觉如何,我是作为学生来听的。因为这样的讲座实际上和中文系的关系不是太大。复旦中文系的学风是研究文学本身,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理论专业,我们和理论专业的交往也不是太多,跟哲学系更加少。所以我相信大家听起来一个会很新鲜,但是其实也会很累,因为这都是进入鲁迅之前的理论准备——其实也不是之前,也是之后的一个反省。所以我想大家还有很多的时间,张老师他是晚上9点的飞机回北京。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9点是一个大概的时间限制。现在我们同学包括各位老师在一起讨论、提问。因为今天是谈鲁迅,所以尖锐点也符合鲁迅的精神。 张业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天讲了那么大的信息量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因为我在这里也讲了4、5年的鲁迅精读课,确确实实是非常“笨”地去读鲁迅的作品,只是可以说没有任何领悟,如果说有的话可能也是些乱七八糟的、不干不明的方法去读,强调的是一个普通的感受,这个层面上去进入鲁迅的文本。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读”吧,这个中学、大学一直过来,包括大学任教也在不断接触鲁迅的作品,但是这样上课之后你得去重新读一下,在这样重新读的过程中会有新的感受。我觉得有一些新的体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那然后鲁迅的一些用心等等。但是这些的话,我今天听了你的演讲以后,我只好说我很惭愧,一直很片面地,然后不成系统的拿到理论的层面上。 我想确实今天是很受启发,包括你今天所说得“小的文学”,比如你说的《阿Q正传》——这个《阿Q正传》我重新读了之后感受最深的就是“大团圆”的细节,在那个情节中好比有一个舞台,在那个舞台上把很多信息、很多的力量聚焦到一个点上,所谓“吃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可以说在阿Q在这个舞台上展现,然后但是所有的这些“狼一样的眼睛”,这种“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我们都能强烈的感受到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将要被这样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所摧毁),而这样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却又非常强大,几乎把阿Q压榨到一个完全没有存身之地的地步、把他“吃掉”。然后在整个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你会发现一点点所谓“人性之光”,这个“人性之光”不是在阿Q的一是要崩散的那一刻发现的,那是那个“吴妈”,用“吴妈”对阿Q的一个注视来表现不是要把阿Q吞噬掉、得到一点快感、得到一点旁观者的满足,它是对阿Q的一个关心,因为它是看向?的洋炮、押送着阿Q的士兵身上的洋枪——对这个枪的关注,他这是对阿Q生命的关注。因为阿Q剩下的、剩余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将由这柄枪来决定。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关注,可是在这个无意识的关注里面,我想说,它就有着《阿Q正传》真正“不敬”里头的人道的关怀在里面。他把整个的一个《阿Q正传》从头到尾嬉笑怒骂可以讲没有给阿Q一点尊严、面子,或者说作为人基本的那么一些东西给全部剥掉了。然后在最后他给了吴妈的一个注视过去,让阿Q作为一个人、作为“文学最后的一点东西”给保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也是说结合到“小的文学”里面去理解。 郜:你有什么问题吗? 张业松:算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吧。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要消化许多信息。 张:我先回应一下。《阿Q正传》那么大一个作品,而且跟整个现代中国民族性都相关的那么一个寓言,肯定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我个人觉得你的这个读法有点“太实”、“太实在”。而这个阿Q我基本上觉得——所以说这也是我说作为文学阅读形式分析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不要“低估”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一个形式、游戏性的力量,它的那个道德因素是非常强大,但是他的道德力量、批判性是通过文学的中介达到的,而文学有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在哪儿呢?我倒觉得《阿Q正传》没有“人道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武断的说法,我跟你这个说法进行讨论。阿Q恰恰是一个“反人道主义”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整个阿Q就是一个“符号”,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阿Q身上没有人性,就是,在阿Q的世界里和人性问题没有关系。 我以前讲过两次阿Q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阿Q几乎就是一个“符号”层面上的一个“游戏”——怎么讲?就是说:阿Q没有姓,也没有名字,也没有籍贯,最后他连一个“行状”都很模糊,就是连有过什么事儿都很模糊。阿Q写的就是个没法“定位”,但这却恰恰是近代中国价值世界倒塌、意义系统土崩瓦解后的最基本的“中国故事”。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怎么讲比讲什么重要。所以《阿Q正传》是很有些“元叙事”的味道的,因为它在讲故事的时候探索讲故事的可能性,即从不可能处得来的可能性。所以小说开篇就讲叙事人的问题是“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名”也没有、“言”也没有——阿Q是一个“不可能性”的故事,这个“不可能”就是给阿Q“定位”“不可能”。其实里面那个感觉我们是相通的,就是所有人都在欺负阿Q,所有人都在不把阿Q当“人”,但是这个不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摧残阿Q的人性,是“命名”——你说这个是中国的社会系统也好、文化系统也好,打个比方,在中国,一个地下的阎王的“生死簿”上没有阿Q,也就是“命名”上就把阿Q给排斥出去了。姓什么?他不许你姓赵,有姓的人都排斥;没有名字,他没有个性——他不是作为“个体性”存在的,阿Q是一个“类”,然后他没有籍、没有认同、没有身份、没有归属、没有家,阿Q是一个游民——可是阿Q是喜剧意义上的,我赞同那种老式的读法说阿Q是“含泪的微笑”,我们觉得辛酸,但是又很好笑。阿Q是个“游魂”,到处被人赶走,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命名系统里面没有他那么一个人,而他拼命的、自作多情的往文化圈子里钻,阿Q比读过书的人还在乎“名分”,比“道德家”还在乎道德,阿Q身上讲“正气”、讲“道德”、讲“男女大防”、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连秀才早就不在乎了,人家都“假洋鬼子”了不是;人家赵太爷肯定是很腐败的一种人;“革命”,人人都在乱搞,也就阿Q把一个根本容不得他生存的“系统”当真了。 最可悲的地方在这儿,这种可悲不在于阿Q这个人物的性格有什么弱点或他的遭遇多值得同情、有多少人性的闪光,而是说这个“系统”就是这样——中国人没有办法为自己命名了,中国人也没有办法来确定自己做的有什么意义,中国人连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连说什么也不知道,而中国人唯一的一个命名方式是一个——它是一个搞笑方式是吧——我的同事胡适之不是在搞“拉丁化”吗、钱玄同不是在搞“拉丁化”吗?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但是“阿”是确定的。反正他叫“阿桂”、“阿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名字里有一个Q——一个“阿”加上一个罗马字母的“Q”,没有这个东西,连阿Q的“可能性”的都没有了——这里不是实质层面的可能性,而是符号层面的可能性——没有这个“可能性”。 语言都要有一个命名系统才能确定“杯子”、“桌子”,命名需要一个前在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都“不许”了,自己否定自己,那这个“无法存在的东西”要来为自己“争一个身份”。阿Q是始终在为自己的身份作斗争,是吧?并不是说现在好像强烈要求评一个教授,要评二级,评四级他就不干了——阿Q同样如此。你说,“我姓什么”你该告诉我吧。你要强调阿Q是要承认它的人性的,这点我同意你,这感觉我们是相同的。但是它这个里面不能“实”着读,而是反映到语言的系统、文化的系统中,整个“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指涉系统”崩溃了,所以《阿Q》在这个意义上是“整个中国的故事”。并不是说阿Q代表了中国人国民性里的“劣根性”,这样讲就太局限了。整个中国、价值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名”和“言”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就崩溃了。阿Q是“名”与“言”的世界里“无法落座”的游魂,是一个意义的幽灵,是传统世界的零余物,所以它让我们感到惭愧和羞耻,因为我们潜意识里知道,阿Q同我们比,是“地道的”或“真正的”中国人,即纯粹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产物。阿Q的悲剧是以喜剧的方式讲的,因为这个系统已经崩坏了,可他还在想尽办法往里面钻,这样不是“愚忠”吗?同孔乙己也差不多——孔乙己在科举制度已经完全空洞化的时候还在那里拾“读书人的面子”,最后给人草草弄死。同样,阿Q既不会也不可能“跳槽”,别人走了、出国了,阿Q是没有办法“动”的——无处可去,也没他呆的地方。“无法命名”,就是这么个东西,这种“悖论”、这种paradox,所有的在这个意义上,阿Q就是“中国”,我觉得这么读是一个从“文学性”出发的读法,因为这样是强调文学在一个“符号”的层面上,重新安排符号的关系,通过这种“符号游戏”来显示某种系统错误。由此这样它还是一个“再现”、一个“表现”,它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反映,而不是直接的反映,而是通过文学的内在的“游戏性”和对于形式的进一层的处理。包括我觉得他和吴妈的关系也是一个“语言错误”,但语言错误往往是最根本的错误,因为它往往是一种“系统错误”的表征,也是集体无意识病灶的症候。 张业松:你的一个“小的文学”,我最多读出了一点“小的意思”。没想到这个“小的”背后真的很“大”,“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郜:我们把问题集中一下,虽然有时间,但是毕竟时间有限制。 同学甲:跟我想说的问题有一定关联的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如果鲁迅写《阿Q正传》写得本来好像是您刚才讲的“有实体性”的东西,然而恰恰通过文学性的形式将这种看起来好像很“实体性”的东西打开了一个生活空间。那么我想问,就是:张老师是怎么进入这样一个深度空间?——也就是说,您的研究怎么走到一个那么深入、开放的境地的? 张:我前面讲的这些其实也在“解”,某种程度上也在交待,我们如何准备同作者有一个平等的“交流”。我是不觉得鲁迅代表什么不可企及的精神高度,也不觉得我在读一个《圣经》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也就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要读到,还有就是从各种“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体论”、“文学的内在性”等等,这并不是一个“热身”、做“准备活动”,这也是一个读到现在为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该怎么样”、“做些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像“脚手架”一样的描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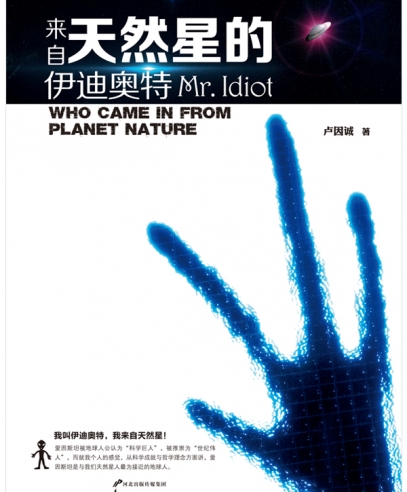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