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我是个低头走路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沉默,呆滞,孤独。看地面看久了人就会变得孤独。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头很大,而且体形瘦弱,支撑不起我硕大的头颅。小时候我总想,要不是我重量级的头,我肯定会被风吹走的。我看人时总是很费力地抬起头,这样子我细小的脖子会承受不了,然后就向右歪,没办法,我的头实在太重了。就这样,我低头走路,歪头看人。 母亲对这一切很讨厌,她说这样子怎么会有出息呢。我搞不懂这跟出不出息有什么关系。母亲在我五岁时,用力摇晃着我的脑袋。她说我儿子的脑袋怎么会这样。她叫我抬起头来。我就抬起头,我看见母亲的眉头拧得跟麻花似的,两道眉毛纠结在一起,就像两团乌云集结在一起似的。母亲说这就对了。我看见母亲额头上的乌云分成两团,向两边散去;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母亲笑的时候,嘴角就像挂着根萝卜条。我很高兴,母亲一高兴我就也很高兴。可是我的脖子开始有些酸痛了,头就不由自主地歪向一边。我看见两团乌云合二为一。 不许歪,你听见没有,不许歪!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母亲把我的头掰正。母亲的手很粗糙,也很温暖。母亲温暧的手捧着我的脑袋,我的脖子一点也不酸,我抬起头看着母亲,我看得到母亲眼底的温存。我想抬起头的感觉真好。我就那样想着,母亲的手又离开了我的脑袋。脖子又酸了,又酸了。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什么办法,我快哭出来了。母亲说算了,你去后山放羊吧。然后我就走了。 我上学以前,总是一个人去后山放羊。我家就三只羊,一只羊爸爸,一只羊妈妈,另一只是小羊。小羊有名字,是我取的,叫小花。我去放羊时总把小花抱着走,就像抱着一个婴儿。我喜欢听她咩咩叫的样子,她用头抵在我怀里,撞得我咯咯地笑。我也喜欢她的眼睛,跟娟子的眼睛一样,忽闪忽闪的,看上去灵巧而温柔。到了后山,我就把小花放下来,我想她肚子也饿了吧,我让她去吃她妈妈的奶。 我一个人到树荫底下。有时候躺着,阳光从摇曳的树叶里钻出来,泛着破碎的光芒。小鸟在山林里唱着不知名的歌。我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有时我低着头看地上成群结队的蚂蚁,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虫。有些会飞的虫子像战斗机一样,落在我身上。我就细细地看它们。它们用细长的腿,在我身上蠕动着。我不知道它们在做什么,可是我很痒。我就咯咯地笑。我一笑它们就飞走了。 有时候我也会想想娟子。我不放羊的时候,总呆在门前古柏树的阴影里。娟子的家就在我隔壁,她总在她家门槛上,不知道玩些什么。娟子看见我就一摇一摆地走过来,那小妮子走起路来像只笨笨的鹅,其实更像一只企鹅,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企鹅的鹅。不过娟子一来我就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娟子满口的虫牙和像喇叭花一样的裙子,我就很高兴。那小妮子。 可是,娟子妈总会扯着嗓子喊娟子回去。娟子妈的嗓门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有段时间,我歪着头看着娟子妈细长而白净的脖子,我就想那么个脖子怎么有那么大的嗓门,真的很怪。
这样的生活我很喜欢,可是在我六岁时,母亲把我送进了学校。我对学校有种莫名的恐惧,那么多的人,挤在一个屋子里,那么多的人,我几乎一刻也得不到安宁。他们哭啊叫地,毫无章法,像一群刮躁的麻雀,叽叽喳喳。 可是母亲叫我上,我就不好说什么了。还有娟子,那小妮子也上学,我就更不好说什么了。 母亲把我的羊卖了缴学费,母亲说上学了要好好读书不用再放羊了。 我们学校是个祠堂,本来是用来祭祀的,文化大革命时用来批斗,后来又当做学校。祠堂房子比普通住房高很多,中间有个院子,总体看来像个四合院,通向中间的院子又有四条回廊,四条回廊像四胞胎一样。这样一来,我的学校就像迷宫,至少对我来说。我每次上完厕所回来就找不到教室了。于是我一间一间地找,等我找到了早就迟到了。那个年轻也有些漂亮的女老师,总会问我为什么迟到?我说我上厕所了。她说课间有十几分钟还不够你上厕所吗?那些毛头孩子就开始笑起来。我讨厌别人在我讲话在末尾用个问号,我更讨厌别人笑我。然后我就不说话,我歪着脑袋看着我的女老师。我觉得不仔细看她是很漂亮的,这样一看就不行了,她脸上有雀斑,一点一点的,像墨水洒落在她脸上。她好像看出我的心思,便很生气,接着就罚我站。 每次罚站总叫我站在靠北边的窗户边,我的头一歪就偏向南边的窗户。我能看见院子里大槐树的树干,看着树干我就仿佛听见树上有鸟儿在欢叫。那个时候我总想猜出树上有几只鸟,我掰着指头一个一个数,于是我发现树上有无数的鸟。我很兴奋,我歪着脑袋,嘿嘿地笑着。老师讲《小猫钓鱼》,她就说我是那只小猫,上课三心二意;老师讲《猴子下山》,她就说我是猴子,她说我见到西瓜就扔掉玉米什么的。总之她上什么课就说我是什么,上《朱德的扁担》时,可是她没说我是朱德。那个女人真的很讨厌。 娟子坐在我前排靠右边一个位子。她上课总很认真听讲,时不时侧过头来看看我,她看着我在课本上乱涂乱画,就翘起她那张吃了很多棒冰的嘴巴,那双美丽的眼睛,倏地一白,就像鱼在水里翻肚皮,在我眼里就是白光一闪,那就像电影里的刀客,白光一闪,对手脖子上就留下一道口子,血还没流出来就倒下了。反正我是怕了那小妮子。她叫我听讲我就听讲。 下课后,那些毛头孩子,就三五成群地去院子里做游戏,什么老鹰抓小鸡呀什么攻城呀什么踢房子呀还有些女生跳像皮筋。我总留在教室,除了上厕所就不出去。娟子也是,她拿着笔在纸上画啊画的。画像大饼似的太阳,画像鸡般的鸟,还画鱼啊水的。我总偷偷地看。有一次,那小妮子还画了个人。那个人细细的腿细细的肚子细细的手细细的脖子,她画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我想还有那么瘦的人啊。接着,她画出了个像南瓜一样的脑袋,把那细细的脖子都压弯了,看上去就像沉甸甸的稻子。那小妮子在那里笑。我觉得那个人在哪里见过,我真的很眼熟。然后我看见她在那个奇形怪状的人旁边画了几笔,她的手挡住了,我没看见,我看见她笑得更历害了。那小妮子笑得真好看。然后她伸了个懒腰。我趁机看到了两个大大的歪歪的字,蚂蚁。那个名字也很耳熟,我想了会发现那就是我的名字。那小妮子她叫我蚂蚁,那小妮子。
我忘了告诉你,我叫马义。本来我是叫马毅的,这是我父亲生前给我取的。可是那个“毅”字,笔画很多,母亲在送我上学前教了我两个星期,我还是不会。其实我都怀疑母亲写对了没有。后来母亲就给我改名了,叫马义。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就那么几画,我就觉得什么事简单就好。 我有很多绰号,都是那女人给我取的。大约有十来个,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她叫我最多的就是小猫。其实我对猫并不讨厌,甚至有些喜欢。但是她叫的我就不喜欢。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的午后,我觉得很适合睡觉,也差点睡着了。我低着头,鼻子快碰到桌子上了。那女人突然喊:小猫。同学们都看着我,我歪着脑袋看着那女人。我记得我眼睛闭了闭,我真的想睡觉。她突然喊:小猫,我叫你呢?你给我站起来。那女人生气了,她生气时脸上红红的,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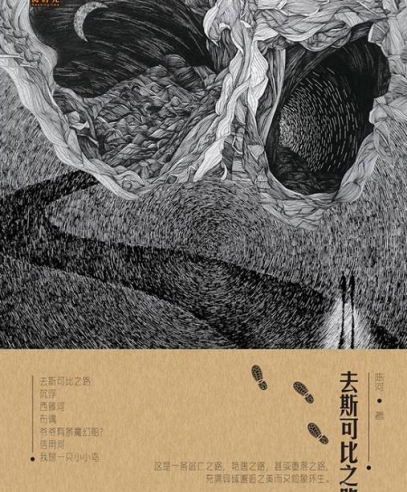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