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当晚,余先生和丁先生转乘了同一列去抚州的动车,丁先生的车票也是早就订好的,两人却不在同一车厢,余先生在5车厢,丁先生在7车厢。九点多,两人一起到达抚州,结伴打了车,到公司事先安排好的宾馆住下。余先生住11层,拐角处的一个三角形房间;丁先生住10层。余先生给丁先生打电话,“老弟,我1117,拐角处,应该是这一层最便宜的房间。”丁先生说:“我1017,也是拐角处,也应该是这一层最便宜的房间。也就是说,你在我头顶,我在你脚下。呵呵!” 余先生嘿嘿笑笑。 抚州比北京热,但并非两人在路上想象的那么溽热。在高铁上,余先生看到丁先生穿了件短裤,笑着说:“挺户外啊!”丁先生说:“南边比北京热,我来的时候在网上查天气了。短裤凉快。” 余先生冲了个凉水澡。他本来不打算招呼丁先生一起吃晚饭,他想一个人下楼找个地摊儿,好品尝一下抚州地方名小吃,关键是静一静,好回忆回忆一路的奇遇。走到大厅,想了想,还是给丁先生打了个电话。丁先生说,他不下去吃饭了,他自己带着吃的。余先生这才想起,丁先生路上吃过东西,北京的芝麻酱饼夹肘子肉。丁先生带了好几个,他吃了其中的两个,还剩下两三个,又塞进了背包。当时,余先生就想:这老弟年轻轻的,倒挺会过日子。像他的性格。余先生坐车从来不吃东西,既不带吃的,也不在车上买,更别提去餐车吃饭。第一,当然是舍不得花冤枉钱;第二,二十年前,余先生去广州,在河南安阳上的车,一下子带了两只烧鸡做路上的干粮。走到湖南长沙,烧鸡就变味儿。他吃不得,也舍不得扔掉。从此,他就是坐一个通宵的车,也不带东西,不吃东西。 哦,原来,我在二十年前就曾路过长沙,只是除了那两只臭烧鸡,对长沙这个城市没丁点儿印象了。 想起丁先生的一大包芝麻酱饼夹肘子肉,想起自己的两只臭烧鸡,想起自己保持了二十几年的习惯,余先生摇摇头。他突然想起,十几年前他在原来的单位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去西安出差,领队一下子在餐车上买了十只烧鸡大腿,他们三个吃了三只,扔了七只。不是他们浪费,是烧鸡腿实在难吃。再说了,公家报销。唉,十几年过去了,咋越混越狼狈?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人民都跨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自己连个芝麻酱饼夹肘子肉都舍不得带。 宾馆楼下的街道两边就有两大溜夜市地摊。余先生看了好几家,问了两个人,他们都说,抚州的地方小吃就是螺蛳。余先生看了看,螺蛳哪里没有啊?武汉固然有,北京也到处都是。抚州出了那么多文化名人,怎么连个像模像样的小吃都没留下?没小吃,就是没文化。唉,文化名人出生在这里不假,他们一生的部分时间却不是在此度过的,所以也就没有给家乡留下能够渲染文化气息的著名小吃。东坡居士在并非他老家的湖北黄冈住了两年,不就给那里留下了著名的东坡肉东坡肘子? 余先生在街口一家摊位上将就着点了一份烩牛杂,还行。烩牛杂算不得抚州地方名吃吧?北方牛更多,而且还是好吃的黄牛,牛杂当然也多,只是少有类似吃法。抚州有没有牛?就是有,恐怕也是水牛,难吃死了。 余先生还喝了一小瓶四特酒,蛮好喝。这个应该算作江西特产。尽管全国各地都有四特酒,到了江西喝四特酒,感觉就是不一样,地道。 三两四特酒下肚,余先生已经有些醉意了。余先生喜欢喝酒,十块钱一瓶的42度二锅头喝一瓶都出不了事儿,喝半斤,不耽误该干啥干啥。咋着三两四特下肚就晕乎乎的?余先生这才又想起,自己在火车上连续呆了十几个小时,已经跑了四五千里,早上走得匆忙,只吃了两个茶蛋。中午在北京西站候车,本来想在一楼一家饺子馆吃饺子,问了问,一份三十多,扭头就出来了。在车上更是只喝水没吃饭。 余先生自豪地笑了。 微醉时分最惬意,也更想喝酒。余先生又要了两瓶啤酒,竟然是雪花啤酒。余先生问:“老板娘,有没有抚州当地产的啤酒?” 老板娘说:“这就是当地产的啤酒。” 余先生看看啤酒瓶上的标签,看不清楚,也就不再说啥。他一边不紧不慢地吃着喝着,一边漫无目的想心事。看看四周,与河南湖北北京没啥两样;听听声音,的确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一句话也听不懂。我姓余的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么多年,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到了这个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五千里啊,离北京五千里,离河南老家四千里。这下,成南漂了,老南漂,老北漂变成了老南漂。 余先生醉眼迷离,看着四周。应该有十一点多了吧?大街上稀稀拉拉的车辆,一边喝酒吃饭的男女,叽叽喳喳,好像在唱歌。这是哪儿呀?车辆好像都是一样的车辆,四个轱辘上边顶着一个乌龟壳,看见人鸣鸣笛;人是一样的人不?余先生盯盯炒菜的中年男老板,盯盯端盘送菜的老板娘,盯盯一名中年女服务员。最后,他的目光在另一张桌子上一位年轻女士身上停了停。 女士朝他这边坐着,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白皙,脸上笑眯眯的。一个蛮传统蛮古典的美女。不过,余先生这个老光棍眼睛看到的,只是一个脑袋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两个鼻孔,和她一边一位先生的五官没啥区别。 到哪儿都一样!到哪儿,男人都是男人,女人都是女人;牛逼都是牛逼,草包都是草包!到上海,到深圳,到美国,到英国,估计到了月球上,也都一个德性! 余先生又盯了盯美女,美女正好也在看他,似乎还冲他笑了笑。她稍厚一些的两唇间露出一口好看的牙,眉清目秀,瓜子脸的下巴颏却圆润。余先生看着她的笑脸,心里暖乎乎的,也还她一个笑。 到哪儿都一样,都是见了尖峭下巴颏的现代美女火烧火燎蠢蠢欲动,想立马弄床上;见了这样传统端庄的古典美女心里暖乎乎的,想抬回家做媳妇。 余先生的目光顺着大街向远处望,北京在哪个方向?河南在哪个方向?北京河南这个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哦,经度相同,都是东八区,北京河南应该也是晚上。喝高了吧? 余先生又盯了一眼美女,他发现,美女也在盯他,笑眯眯地,一口洁白的牙齿和灿烂的笑脸像盛开的牡丹花。余先生又冲他笑了笑,笑得很开心。美女身边的先生看看余先生,也冲他笑笑,似乎也很开心。余先生知道,自己就是当着一位丈夫的面冲人家媳妇笑,人家也不会怀疑吃醋,余先生笑起来,有点儿像弥勒佛,好多人都这样说。没有哪个人会把弥勒佛的笑往歪里想。 停一会儿,余先生又盯了一眼美女,她正低头啃一块骨肉,他只看见一头长长的秀发,在明晃晃的灯光下,亮晶晶的。刚才那股暖和劲儿又在余先生心里翻腾。突然,他想起了招聘单位那个副总说的给房子给配偶安排工作的优惠条件。他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来对了! 抚州的确盛产美女,这不,刚到这儿就遇见一个。他又偷偷瞄了那女子一眼,女子已经啃完了骨头,正端着一杯啤酒扭脸和其他人说笑着,余先生看到,她的秀发绕过耳际,在脑后扎了一个他不知道名字的发型。 来对了!又是给房子,又是负责安排配偶工作。恐怕这边的女子,比如就像对面这位女士,也不是轻易就能到赣南生化那样的高新技术企业上班的吧?咱来到这儿,不但有房子了,肯定也会有成队的美女向咱眉目传情,多诱人的候选老公啊!哈哈,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这样暗自谐谑一番,余先生又怪自己:别那样调侃你未来的媳妇儿!你不是找家啊?光有房子,仅仅是个窝儿;有了女人,有了两情相悦的女人,才算真正找到了可以把心安置在里边的家啊! 两瓶啤酒也下肚了,余先生的头脑竟然越来越清醒。不是因为来到了一个陌生地方有点儿兴奋才越喝越清醒,以前,他也有过很多次类似的体验,超过半斤,越喝越清醒,不是假清醒,是真清醒,清醒得一下子就找着了北,一下子就找着了自己,没喝酒之前稀里糊涂的同事熟人之间的冷热,尤其过去咽下去的窝囊气,一件接一件从打开的心门中钻出来,站在他跟前,和他面对面相互注视着。“妈的!那么大一口窝囊气,我那会儿竟然生生吞下去了!”“我真是个混账东西啊!我那会儿咋就那么傻屌神经咧?那样没心没肺的事儿我都能做出来!” 不过,这会儿在盘里捞着最后几块烩牛杂,余先生没有骂谁,也没骂自己。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位女士,女士冲他笑笑,他也冲她笑笑,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想着是否最后吃点汤粉。 马路对面的地摊上,一名歌手正在给客人唱歌。余先生睁大开始迷离的双眼,隔着马路看过去。是一名男子,看不清面目,只看见他上身穿着白衬衣,被地摊上的灯光照着,泛着幽蓝的荧光。他怀里抱把吉他,自弹自唱。唱的啥?余先生很喜欢流行歌曲,他觉得他比小青年儿还熟悉流行音乐,却听不出这是哪首歌。应该是他自己的原创吧?抚州的确有文化,就连街边卖唱的都会原创! 余先生低头发了一会儿呆,抬起头的时候,那名歌手站在了他的桌子前。他也不说话,径直自顾自弹唱起来;唱的啥,余先生还是没听过。 余先生看看地摊老板娘,老板娘走过来,摆着手撵歌手:“走吧,走吧!这位先生一个人,不想听你唱歌!” 歌手看看老板娘,继续自顾自地弹唱。余先生看着歌手,在马路对过看着白白的衬衣,这会儿再看,上边粘着一点点的污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还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皱巴巴、脏兮兮。滑稽的是,他穿着一条比领带更鲜艳的大红裤子,就像马戏小丑穿着的那种灯笼裤。他的发型一绺绺树立着,倒不像因为好多天不洗头,应该是抹了啫喱水之类,然后着意梳成这个样子。但从脸上分明可以看出,他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多岁小五十儿。 老板娘又吆喝他,余先生冲老板娘摆摆手,乐呵呵地说:“我喜欢听歌,让这位艺术家唱吧!”老板娘笑了笑,嘴里嘟囔一声,走开了。 歌手唱完,站在余先生面前。余先生笑着问他:“老兄,你是不是白天也跑保险啊?” 歌手一只手理了理自己的领带,笑着说:“是啰是啰!我白天跑保险,还直销一种花粉保健品;晚上就到夜市上唱歌。老板,再来一首吧?” 余先生笑笑,掏出钱包,他看了看里边的一张五十的钞票,犹豫了一下,抽出一张十块的,站起身,身体晃了晃,双手把钱递给歌手。 歌手双手接过钱,连声说:“谢谢!谢谢!遇着贵人啰!贵人,承蒙您欣赏我的原创,我就再给您弹唱一首,免费,也是原创啰!” 老板娘又走过来,不耐烦地呵斥歌手:“走吧走吧!唱了一首了,也给你钱了,还烦人呀?” 余先生也说:“谢谢你,老兄!不耽误你生意了,你去别的桌子上表演节目吧。” 歌手立正,右手放在右脑际,给余先生敬了个礼。余先生一边说“不敢当!不敢当!”一边嘿嘿笑着。 歌手瞅瞅一边的空桌子,几名顾客刚刚走开,老板娘还没来得及收拾。他走过去,端过来半盘吃剩的花生米,双手放在余先生面前,“老板,不成敬意,借花献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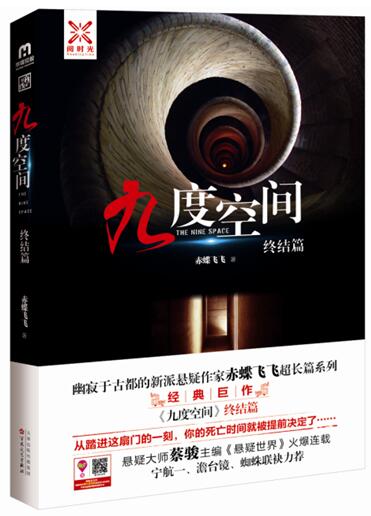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