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子眼睛近视,命子的听觉却分外灵敏。权且静下来的他却分明听到浊流激溅中的蹊跷之声。
五叔,你听——,好像水中有其他声音,像是人的呼救——
五老汉摇摇干瘪的苍老的脑袋,表示没能听清,他已无力去谛听和分辨了。
那微弱细小的不绝如缕的呼救声却越过猛烈的浊涛钢针一样刺扎着命子的耳鼓。
不对,有人呼救!五叔,你好生歇着,让我游进水里察看一下。命子说罢扑通一声跃入水中,逆水朝前游去了。
老三被水流猛冲下来后,头部和身体多处碰伤,漩涡中的他无力挣扎,只等着洪水摆布了。
命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漩涡里拖拽起他时,才惊讶地认出这是老三。他原以为老三早跑出了井口,打点着东西准备明天登上去河北的车呢,谁料到他也没有逃出罪恶的洪水。
老三——老三——
无论命子怎么叫,老三像一摊泥,软在命子的背上。
在五叔的用力搀扶下,命子才把泥一样的老三平放到石台上。
五叔和老三勉勉强强挤在窄小的石台上,命子只有背靠着石台,和马骡子一起,双腿浸泡在黑浊的水里了。
这一刻,命子倒没有了最初被浊水吞噬的恐怖感了。那会儿,只有他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巨大的灾难和黑暗,而现在,面对灾难的是连马骡子在内的四条生命了,命子心里,有了一股踏实和依靠。尽管五叔苟延残喘,老三人事不省,马骡子是不晓人事的畜牲。另外,还有一段粗粗的松木,一把冲下来的钢铣。
在这个作业面的最深处,在这个煤窑的最底端,在距地面八百余米的幽黑而此时灌满了浊水的一隅里,三人一畜四条生命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只有水流在拍击巷壁的咕咕声和从主巷钻进空巷的拐弯处的漩涡的拍击声一阵阵地传来。它们绝非往日的劳作声,那种声音充满了有条不紊的紧张,洋溢着艰苦获取和顽强生存的欢愉,而此时居心叵测的声音充斥着不怀好意,弥漫着恐怖和死亡的黑色气息……
突然,命子发觉石台上的老三动了一下,他低头细看,才瞅见老三的脸上涂满了鲜血,一股血流从湿漉漉的头发洇出来渗出来,汨汨地流向脖颈下。
命子摸出裤兜里的手帕儿,用力缠裹住老三脑袋上的伤口。
老三于昏迷中被疼醒了,他蠕动着企图爬起来,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动作,他已没有爬起的可能了。
命子……命子……快扶我上去,上窑去,……孩他娘等急啦……明天到河北……我,不能耽误的,那边……还等我一…·。
命子轻轻揩着老三脸上依然流淌的血痕,慢慢安慰说老三,你别急,等水退了我会扶你上去的,这边,还有五叔呢——别怕,窑上的人,也会设法搭救咱们,你就好生等着吧。
命子这样安慰着老三,脸上却笼着一层无奈。从水流的沉闷声响里,他判断出上面依然在朝窑下猛灌呢。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他们盘踞的这屁股一样小的石台上,再不敢让大水淹没了。
老天爷——,你就行行好吧——
命子在心里祈求着,嘴里却念叨出来了。回答他的,却是那愈来愈充盈的汩汩声响。
时间,在这个潮湿而干涩的黑暗里浊水一样地汪泊着,它似乎疲劳了,停滞了,凝固了,像此时命子的思维一样,没有跳跃没有激越,没有流动,却同脚下被高气压顶住了的水流,黑沉沉了无生机,惟有混沌的杂物和一层黑色的煤尘在沉沉浮浮。
命子困乏了,一切都定格在黑色的迷朦里。枕着静止下来的老三的胸腹,命子极快地进入到轻俏的梦乡里。
妈——,我饿啦,饭还没好么?
问完这一句,命子笑了,妈已把细长的面条切好在案板上啦,炒菜锅里,正氤氲着豆腐粉条白菜和猪肉片子的烩菜的奇香呢。
你爸挑水去啦,你爸回来,咱就下面。妈擦了把额上的汗,慈祥地笑着。
我接我爸去——
长长的土坡,弯弯的小路,爹挑一担水悠然地往回走,爹的口里似乎还哼着一段老蒲剧。
命子听出那是《水漫金山》的段子。
命子执意要接过爹的担子,爹却不让命子挑,一拽一拉之间满满两桶水洒了出来,洒了命子一腿一脚——
命子觉得两腿两脚湿得难受,湿得发痛了。
命子一拽筋,被疼醒了。
醒咧,命子?!
五叔此时无精打彩地盘在石台上,手却在身边的马骡子背上一下一下捋毛儿呢。
我梦见水啦!凉得我好难受呢。
命子说:
嗬——,梦水好啊,梦水是财呀,咱们不仅能从这水窑里出去,出去后还有大福哩!
五叔的小眼窝里迸出两粒豆子般的欣喜。
哎!能出去就谢天谢地啦,还敢指望什么后福大财的!
听完命子的话,五叔的嘴蠕动几下,一张核桃皮一样的老脸上现出一脸的豪气……
那年——,嗯嗯,我和你一样的岁数,在豁子里那眼煤井下受苦,那是一眼竖井,深七八丈哩,那一天我一个人提前到了井下,想早早炸开岩层,好让后到的工友们顺当当地朝上提煤,哎,那会儿年轻,火气旺盛,就不把苦哩累哩危险哩当一回事情。我一人下到井底,在上午凿好的炮眼里塞好了炸药,安上了导火索,然后就小小心心地点燃了。看着导火线头上的一点火红和飘散的一股烟雾,我知道我得赶快抓住井绳朝上爬了。
要在往常,点燃了火索后,井上的人就会很快把我吊上去的,那天我使了个大胆,只要点了捻子我顺着井绳攀个三四丈高,炸飞的石块是不会砸到我身上的。谁料到,当我的双手抓住井绳刚要上攀时,窑井的井壁塌方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药没炸,却有一大片煤石塌了下来,我只觉得双腿麻木,两耳鸣响,腿被石块砸伤了,那时候已经动弹不得,我心里怕呀!心里急呀,再不赶紧朝上攀,那点燃的导火线会很快接近了炸药眼子引起爆炸的,那会儿,小命就报销啦……我奋力从煤石堆里抽出两腿,那已是两条血肉模糊的腿了,鲜血带着煤屑把裤子浸洇得一片殷红。
受伤的两腿是一点劲都用不上了,斜倒着的我,用两手去抓井绳,身子一动,两腿就钻心地痛,那会儿不知是急的还是痛的,脸上身上出的汗水象遭了暴雨猛淋。
为了活着,我得上去,要上去,就得先抓住那根粗粗的井绳。而眼下,我探不着井绳,粗粗的井绳像一条树根动也不动一下,如果能左右一晃,晃过来,离我就近些。
一个激灵,我拾起一块煤石,对着井绳使劲砸去,井绳晃悠开了,晃悠到身边时,我一手紧紧攥住了它,我像捞着了一根求生的稻草,我也弄不清自己哪里来的恁大劲儿,双手朝上一把一把地攀,就把痛疼的双腿双脚从石堆的埋压里拽拉出来,一出来,身体就轻松了,我一节一节一把一把地往上攀着,只要上一节儿,我就多一份安全感,上呀,攀呀,这会儿,麻木和痛疼轮到我的双手啦,要知道我全身的重量就在我的两只手上,吊着,还要用力上攀,而左右手的相互替换之时,全身的重量就仅在一只手上了……
我弄不清攀上多高了,看看下面,黑洞洞的已经很深,看上面,井口的一方白色依然离我很高很远,我清晰地看到我两手心里的肉被粗砺的麻绳划割破了,起先翻开的是一片又一片的白肉,白肉很快泛红了,血像泉眼一样汨汨地涌出来,一条一条地染在粗粗的井绳上。
稠浓的血给我的是一种残酷的力量,我知道我已经累得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啦,只要稍一松劲稍微缓一口气,我就会从长长的井绳上滑下去或者干脆掉下去,掉到我刚刚攀上来的幽深的黑暗里,……我不能松劲儿,我把牙齿咬得咯嘣作响,因了使劲儿,我把一颗后牙咬得破碎了,血沫连同破碎的牙片从嘴角溢出来。我一点一点地攀,一点一点地上,我知道,上一点,我就离井口近一点,上一寸,就距危险远一寸……
我忽然听到井台上面有了人们的说话声,有了发现我的惊呼声——
快朝上吊我——
我只喊了这一句,就动不了啦,双腿双手紧紧地抓着挟着井绳,刚刚被人吊上井口,井下就传来一声巨大却沉闷的爆响,轰——那包被埋在煤石下的炸药,终于燃爆啦,我却晕死了过去,我刚被人们吊上井口,全身就泥一样瘫软了……
命子,五叔是死过一次的人啦,五叔的命大——,五叔现在是啥也不怕啦,咱都能上去的,连同五叔的这条马骡子——
幽黑的沉闷里,五叔的话掠过黑黑的水面,朝远处荡去,五叔的话又如同这七月井上的一缕暖风,适时地薰着命子年轻的心。
他转头深深地瞅一眼这个佝偻卑琐的小老头,不知道他的身躯里居然蕴含了不可估量的生命之力。
对了,五叔,我们能活着出去,能活着出去,绝对能!命子坚定地说道!
老三一声痛苦低微的呻吟后,身体抽搐起来,而命子浸泡在水中的双腿也十分厉害地抽起了筋。命子顾不及自己,他把脑袋凑近了老三。
老三——老三——好些么?
命子把手抚在老三额上,老三的额上像着火一样发烫。
老三发高烧啦,命子看到老三的嘴唇在不长的时辰里泛紫泛青且暴起了白皮。
五叔,这可咋办?命子问。
没人回答;
命子看到五叔此时闭了眼似乎睡觉了。
命子摸出手帕,那是兰兰春季里特意送给他的,毛绒绒的,帕儿中间还绣了一对飞翔的大雁,命子顾不及多想,拿手帕探下身去蘸蕴着浊水,一点点喂给老三,拧给老三。
老三微启嘴唇,帕上的水,流进了他的嘴里。
我得上去……我要,到河北……我要,回老家河南……回去……
老三含含糊糊呢喃着,却一把攥住了命子的手,命子的手居然被他捏痛了。
我,得,上井去……,扶我……上去……老三下意识地一动,扑——嗵——一声,居然从窄小石台上滚了下去——
水花啪——地溅起来,吓了一旁的马骡子一跳。
五叔——,快帮我一下,我腿肚子抽筋扶不起老三啦。
五叔的小眼窝却没有睁开,五叔阴阴地说,命子,你也该到石台上躺会啦,老三一个河南流窜人,又受了大伤,我看,——就——就——
命子似乎不相信这是五叔的话,平时五叔不吭不哈,埋着脑袋像他那匹马骡一样死受活受,静默得如同窑下一块无人理睬的煤石,月底到矿长那里结账时,五叔是分文必争的,有时对人们忽略了的一天半晌大家都不去认真的工钱,五叔尖着苍老阴沉的嗓门能和当事人吵个大半前晌。抠门倒不怕,人都珍惜自己的血汗自己的劳动哩,可是,对同一个煤窑里的工友咋能说出这种话来?命子有些纳闷。
快!五叔,快帮我一把,高烧的老三不敢泡水的!
五叔极不情愿地跳下水来,帮命子去拽老三的胳膊。两人费了很大气力,才把老三扶上石台。
我,我是说,命子,你也该上来躺一会儿,河南人眼看不行了,这会儿,你可不能丢了自己的……
五叔,你咋能这样?!
命子反诘。
都啥时候了,你还顾及一个外人?他眼看就不行了么,五叔嘀咕着,又爬上了石台,他蜷缩成一团儿了,衣服上的水滴嘀哒哒流到台下的黑水里了。
命子没去理会五叔,却感到老三发烫的身体再不能在冰冷的石台上躺着了,他转过头来,他看到了身边的马骡子柔软温热的脊背。
对,得把老三扶上骡子背,让他趴在骡背上,骡子的体温可温热他的衣裳他的身体。
当命子把他的想法说给五叔的时候,蜷缩一团儿的五叔,倏然间坐起了身子。他破铜锣一样苍沙的嗓门居然嚷嚷起来。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让一个外路人骑到我的骡背上?亏你想得出哇,我养马骡六七年,还没舍得骑它一骑呢!
老三发高烧,人事不省啦,在骡子身上,烘干他的衣裳……没等命子进一步解释,五叔的小脑袋摇得像货郎鼓。
在那一刻里命子对五叔这个小老头极度地轻蔑了,难道畜牲比人还重要么?你这样娇贵你的骡子,让它在地上好了,你怎么又让它下这黑洞洞的窑下受苦呢?
命子冷冷地问他。
我在地上马骡子就在地上,我在窑下,马骡子就在窑下,我和它寸步不离呢。五叔说罢又起身给他的马骡子顺毛了。
命子照护着老三,不再去理那五老汉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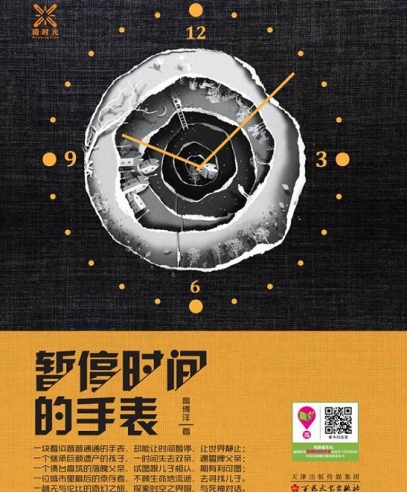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