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色渐浓,吃了香椿的新芽,口齿清爽,很想读一本温暖的书。正巧接到张守仁先生赐赠的《永远的十月》,素雅的封面上,有一丛兰花,幽幽地发出暖意,一如早就定下的一个邀约,便借“五一”的三天假期,独居一室,静静地耽读。
张先生的文字真是纯净,读的时候,好像幽暗的内室有阳光一缕一缕地照耀,从始至终,内心都涌动着一股暖流,盈满得既感动又忧伤。这种感觉,一如早年被爱情俘获,因为感情纯粹,所以感动;因为世态浇薄,所以忧伤。
张先生的笔致,至纯至性,唱的是文学至上、精神至上、感情至上的心灵大歌。他唱得不管不顾,一如古田野上的荷锄者,甘于庄棵,陶然击壤,“帝力于我何有哉”!他很自足。
张先生是《十月》的创办者之一,享有“四大著名编辑家”的文学声誉,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文学历程的亲历者,由他之手,推出了一大批当代文学名作和当代文学名人,与《十月》一起成长,与《十月》一起辉煌,可谓阅尽文坛春色。在风云际会之间,他始终在场,因而有历史见证的资格。他见多了文坛上的世俗、功利、争竞和阴私,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文坛上的世故老人,借名家以自重,借名篇以称雄,在摇曳之间,沾沾自喜。然而,他的笔触总是那么低调,以文学老农的身姿,朴实地叙写壮株之所以长成,好收成之所以得来,写得贴心贴肺,一派敬重。
因而他爱笔下的每个人物,以十分的体恤,道出他们的甘苦,好像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亲人,即便是瑕瑜互见,也只是说好;他也爱每篇他推崇过的作品,即便是在时间深处,有了明显的破绽,也不忍珠玉蒙尘,而是怜惜地拂拭再拂拭,让其兀自发光。
他跟汪曾祺可有一比,都是温暖的底色,他们都不居高临下地臧否人物,评藻物类,而是平等相待,感同身受。不同的是,汪曾祺疼爱的是他想象中的事件和人物,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人间送小温”;而张先生疼爱的是与他相遇的 和作品,以温厚的胸怀,为文坛道珍重。相形之下,汪曾祺笔下没有恶人,在张先生眼中,遍地是好作品。
其实文坛早已不是一块净土。市场规则,功利诱惑,红尘滚滚,此消彼长。但从张先生的字里行间,读不出一点渣滓,反而是满眼亮色。掩卷沉思,反观其人,发现这是他的文学观念使然。在文坛和文学之间,他看重的是文学。文坛多的是名利与是非,只有文学才直逼心灵。在文坛之上,他站立;在文学面前,他匍匐。所以,文坛虽闹热,他始终是个旁观者;文学虽冷落,他却矢志不改,虔敬地投入。他是文学的信徒,文学的宗教树上,枝枝柯柯都有菩提佛性,都散发着神圣之光。因而他有定力,“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对名家不谀不媚,对无名者不轻不贱,谁写出好作品,他都平等尊崇,大声叫好,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深夜,铃声猝响,兀然惊魂。家婆甚恼,对着话筒训斥道:“你是谁,还让不让人睡觉?”那边赧然低语道:“对不起,我是张守仁,找凸凹。”隐约中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心中一惊,赶紧把电话抢过来,示意家婆不要吱声,然而她还是嘟囔了一句,“真是的!”我不得不说,“张老师,对不起,我夫人她不懂事,请您多担待。”他却不迭地说,“是我不懂事,哪有半夜三更给人家打电话的,然而你老兄写了那么好的散文,我忍不住要吱声。”于是就有了终生难忘的四十分钟“午夜真谈”,他对我的作品如数家珍,大加赞誉,弄得我羞愧难耐,大汗淋漓。之后,就是推荐,就是公开鼓吹,热情洋溢,不遗余力。
事实上,不少青年 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张先生真像无私的阳光,只要你是庄棵,他都要送去温煦的照耀。
为此,我在许多场合,都发出真心的感叹:一如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在当代中国文坛,张守仁先生也许就是最后的一个文学赤子了。
记得蒙田说过,儿童的天真不是真正的天真,只有成年人的天真才是真正的天真。梁遇春就此衍发道,儿童的天真,是一种生物本能,因为他不谙世事,不知利害,便可爱而不可贵。只有成年人的天真才是可贵的,因为他阅人无数,历经沧桑,已知轻重,已知进退,再天真而处之,便是一种伟大的操守了。以此推之,张先生的赤子形状,乃是一种人生品格,在他那里,文字无欺,精神高贵,文学神圣!
张先生的赤子情怀,固然源自他的出身、他的性情和中国诗书为上的文化传统,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他,得天独厚地承接了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的濡染和涵养。俄罗斯文学家,总体地不畏权贵、不惧苦难、不堕俗志,追求以文学为本的自由言说,铸就了思想、精神和情操为上的内在品质。托尔斯泰的宗教情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自审、赫尔岑的灵魂拷问、屠格涅夫的阳光心态、魏列萨耶夫的悲悯体恤,都让人感到,文学是个伟大的存在,是人间道德之上的道德,是世俗伦理之上的伦理。于是,他们爱文学,胜过爱生命!他们也都是一群“天真”与纯粹的人——他们在文学与人生之间划上了等号。
不然,就不会有果戈理觉得《死魂灵》第二部没有写好而愤然焚稿,屠格涅夫曾真诚地说道,读一读果戈理,在俄罗斯大地上走走,很好。
我也由衷地说一句,嚼一嚼京西的香椿,读一读张守仁,很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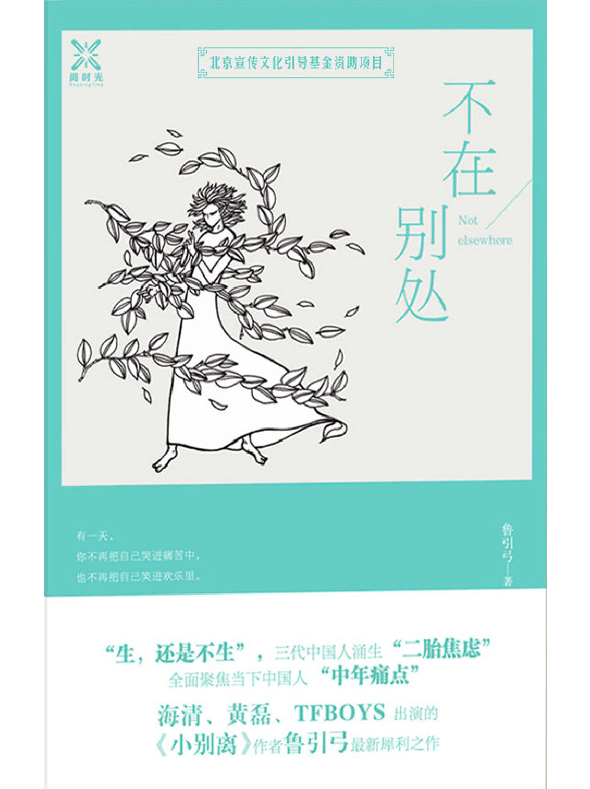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