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走下楼,到汽车站,上车,渐渐离开镇子,我望着车窗外的广大的土地和天空。自然多么辽阔,而人类的城市和乡村,只占很小一部分。自然如此博大,人类却局促在自己的狭小世界里。 我看到我正在离开我生活的地方:镇子。住宿楼。学校。我看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语境。现在,我进入了另一个语境:这是大自然--人的语境,我仿佛是唯一面对无限自然的人,这个语境多么辽阔。 我突然发现,我过去的单位生活是多么可笑,我生活在单位独特的语境里,远离自然,陷入一个狭小的世界。我们常常被洗脑,一周两次例会,传达文件,指示,大官员的,大大官员的;小官员的,小小官员的,我们被灌输着统一的思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象邪教或传销对人进行精神控制一样。正是这些文件会议报纸限制了我们对无限天地敞开的思想。他们正是用这一套对人实行精神统治。这就是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所说的“词的暴政”呀! 我把这一看法对诗人雪峰谈了,他说,通过这种方式,把你和他们连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共同的价值观,荣辱观,与他们同喜,同怒,同哀,同乐。 我想起卢梭,他认为,自然是美好的,人类是丑恶的,他崇尚原始人的生活。他真是先哲啊!他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人,只有回到自然,才会回到人本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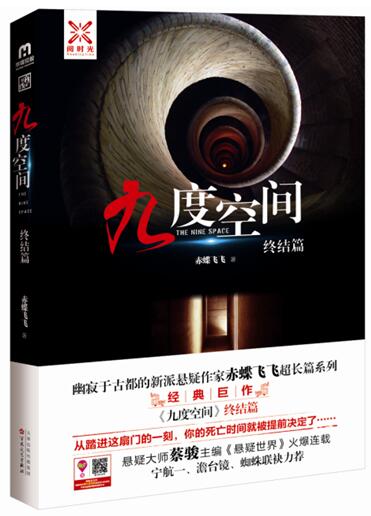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